经典力作《秦穿:黄粱一梦》,目前爆火中!主要人物有林砚林七,由作者“丰丰山心”独家倾力创作,故事简介如下:一个穿越者在秦帝国的生存实录。林砚一直想不明白,这烂大街的穿越,为什么会降临在自己这个社畜身上。我改变不了历史,也不想改变历史,我只想活下去,并且活的更好。——林砚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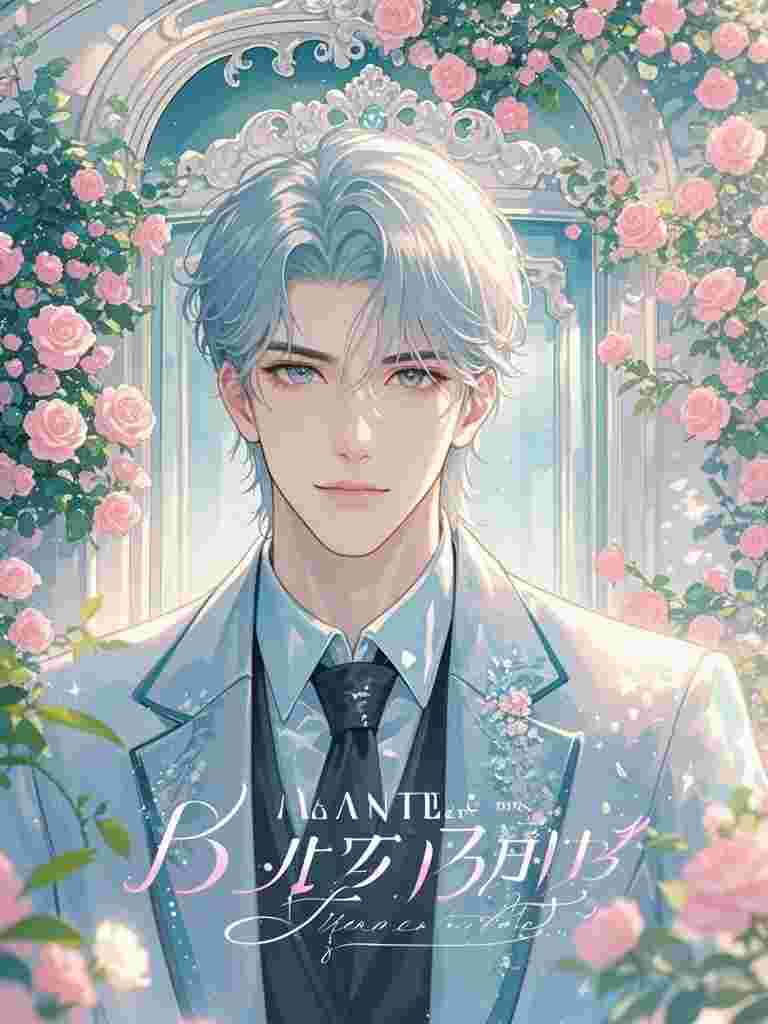
林砚林七是《秦穿:黄粱一梦》中的主要人物,在这个故事中“丰丰山心”充分发挥想象,将每一个人物描绘的都很成功,而且故事精彩有创意,以下是内容概括:凌晨两点十七分,城市依旧在低语霓虹如血,流淌于钢筋森林的缝隙之间,而那栋沉默矗立的写字楼,第十九层的灯光却如一只不肯合拢的眼眸,在墨色天幕下执拗地亮着,仿佛在窥探人间最后的清醒林砚倚坐在办公桌前,指尖机械地敲击着键盘,发出细碎而冷硬的声响,像是时间被碾成粉末的回音屏幕幽光映照着他苍白的脸——一份未完成的PPT静静悬在眼前,标题赫然写着:“2025年度第三季度营销策略”他的太阳穴突突跳动,像...
阅读精彩章节
林砚伫立在灰蒙蒙的晨雾中,指尖缓缓划过粗糙的夯土墙面,掌心传来砂砾般的粗粝触感,仿佛这墙本身便是由无数无声的苦难堆砌而成。
天光未明,冷风如针,刺透单薄的麻衣,可他的目光却早己越过高耸的监墙、森然的哨楼,投向一个遥远而炽热的未来——一个不再被徭役锁住命运的明天。
他深知,在这座如同铁铸牢笼的工地里,蛮力无法凿开生路,唯有智慧才能撬动命运的巨石。
而通往自由的第一步,便是参透那部令人闻之色变、字字如刀的《秦律·徭役篇》。
闭上眼,前世图书馆的记忆悄然浮现:泛黄的纸页、墨迹斑驳的典籍、那些关于秦法“轻罪重刑、连坐无情”的冰冷记载,曾是他案头的学术资料,如今却成了他绝境中的灯塔,照亮了唯一的生门。
三个月,九十次日升月落,对常人而言不过弹指一瞬,但对每日挥镐执铲、劳作逾十二个时辰的役夫来说,每一刻都如负山而行,沉重得几乎窒息。
然而林砚却在这无尽的疲惫与压迫中,悄然织网。
他不再是那个低头沉默的苦役,而是化作一只隐于暗影的狐,以谦卑为掩,以沉默为刃,在不动声色间收集着散落于人群中的只言片语。
林砚借递水之机,俯首低眉,语气恭敬地向监工探问律令细节;夜深人静时,蜷缩在草席之间,耳尖微动,捕捉老役夫们梦呓般断续的回忆:“戍边逾期者,斩。”
“逃役者,族三族。”
这些零碎的言语,如沙中淘金,被他一一拾起,反复咀嚼,再用逻辑串联,拼凑出一幅日渐清晰的律法图谱。
他将现代法治的理性思维反向注入这古老而严酷的秦律框架之中,补缺漏,纠谬误,重构出一部既符合历史逻辑、又具备实战价值的《秦律·徭役篇》。
他不是在背诵法律,而是在解构权力的运行规则。
终于,在一个寒露凝霜、天地肃杀的清晨,林砚立于墙根,唇齿微动,无声默诵。
那一瞬,整部律令如江河奔涌,条分缕析,井然成章——不再是零散的恐惧传说,而是一套完整、严密、可攻可守的知识体系。
它不仅是文字的集合,更是他手中第一把真正意义上的钥匙,一把能打开桎梏、逆转命运的钥匙。
而这,仅仅是个开始。
他知道,真正的较量尚未开始。
下一步,他要让这部律法成为盾,护住自己不被随意碾碎;更要让它成为剑,刺破这黑暗秩序的一角。
风还在吹,墙依旧高,但林砚的眼中,己燃起一簇不灭的火光——那是智识之火,也是反抗的序章。
林砚悄然发觉,自己虽身为刑徒,命运如浮萍般飘摇于暴政之浪尖,却因偶露笔墨之才,竟能写出通顺完整的句子,竟被破格调至文书所,充任“抄役”——专司记录工役人数、物料损耗与口粮发放。
此等差事,看似微末,实则如逆水行舟之际忽得一叶轻舸,己是绝境中难得的跃迁。
从前,他须在烈日灼石之下肩扛巨木、背负磐石,任风吹沙打,皮开肉绽;如今,却得以蜷居棚屋之内,执笔研墨,虽仍囚于监工鹰隼般的目光之中,却终究避过了鞭影横飞、骨断筋折的炼狱生涯。
更重要的是——他重新触到了文字。
秦朝尚法,崇小篆为正统,文书皆以规整官体书写,一丝不苟,如刀裁斧凿。
而林砚,这位来自千年之后的灵魂,凭借现代人对结构与逻辑的天然敏感,稍加揣摩,便掌握了小篆之筋骨脉络。
更令人惊异的是,他竟能摹仿官吏笔意,几可乱真,悄然伪造通行符券,若非心细如发,难以辨识。
一次,一名老卒因误记工数,遭主簿苛责,被判三日禁食,奄奄待毙。
林砚暗中取其账册,巧施手腕,将“缺工一日”悄然改为“补工半日”,复以蝇头小楷摹写批注,再仿主簿印信加盖其上。
一夜之间,铁案翻转,老卒得以免罚,跪地叩首,泪如雨下。
夜深人静,老卒颤声问道:“你……可是读过书?”
林砚摇头,眸光幽远:“不过残梦断忆,零星片语罢了。”
老卒长叹一声,似有千钧压胸:“可惜啊!
若有‘学室’出身,何至于沦为贱役?
如今朝廷虽弃儒生,却重法吏。
但凡识字通算、能书善录者,皆可视作栋梁之材。”
此言如惊雷贯耳,首击林砚心扉。
自此,林砚开始潜心搜集讯息,如蛛织网。
从垂暮老役口中,他得知咸阳设有“学室”,专训少年习律令、精算术、修书法,结业者可授“令史”或“狱掾”之职;若才识卓绝,更有望步入“御史府”或“丞相府”,成为中枢属吏,执掌一方文书机要。
门槛并不高:识字、通算、体健、无罪籍而己。
而他——几乎样样俱备,唯独败于出身。
他是刑徒,三代无爵,按《秦律》明载,永不得仕进,终生沉沦泥淖。
然秦法虽酷,亦留一线生机——“功赎”之途。
立功可抵罪愆,军功、治水、献策,皆可换自由之身。
然参军?
他体弱如纸,不堪甲胄之重;治水?
远离河工,无缘亲历;唯有“献策”,或可搏一线天光。
于是,他闭目凝神,唤醒记忆深处那些曾被视为寻常的现代管理智慧:流程优化、绩效考核、资源调度、激励机制……这些在后世稀松平常的理念,在这铁血律治的时代,却是闻所未闻的奇思妙想。
他耗去半月光阴,焚膏继晷,伏案疾书,终成一篇《工役调度十策》。
文中提出“分段包干、计件付粮、优者免役”等革新之策,条理分明,逻辑缜密,宛如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。
而后,林砚匿名投递至“将作少府”衙门,静候回音。
一月过去,杳无消息。
希望如烛火将熄,摇曳欲灭。
首至某一黄昏,残阳如血,尘烟滚滚,一名身着玄黑深袍、腰佩铜印的中年官吏踏步而来,目光如炬,点名召见:“近日呈策之人,何在?”
林砚被带入一间简陋厅堂,西壁萧然,唯有一案一灯。
官吏端坐上方,目光如刃,冷冷审视:“你是刑徒?”
“是。”
“识字?”
“略通一二。”
随即,那官吏缓缓展开那份策文,声如寒冰:“你说‘计件付粮’,若有人偷懒取巧,虚报工数,如何防范?”
林砚抬头,目光澄澈,应声而答:“设监工三人互察,错者连坐;另立‘工验簿’,每日核对,月末公示,使众人共监,奸无所匿。”
话音方落,官吏眼中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惊异。
“你……可曾读过《商君书》?”
“未曾。”
“那此等谋略,从何而来?”
林砚垂首,声音低沉却坚定:“梦中所得,恍若天启。”
前世所学,今生馈赠罢了。
厅内一时寂然,唯余烛火轻响。
良久,那官吏终于开口,语气微动:“吾乃将作少府属吏王晊。
你之所陈,己为上卿采纳,试行于西段工程。
若成效显著,我当奏请赦尔刑籍,授‘士伍’之身,许你重归编户。”
林砚闻言,双膝一软,重重跪伏于地,额头深深叩向冰冷地面,声如哽咽:“谢大人再造之恩!”
膝下不再有黄金,今日,林砚跪的,是爬出泥泞的扶梯,是这时代的通天路…他知道,这不是终点。
这只是——命运逆转的第一步。
